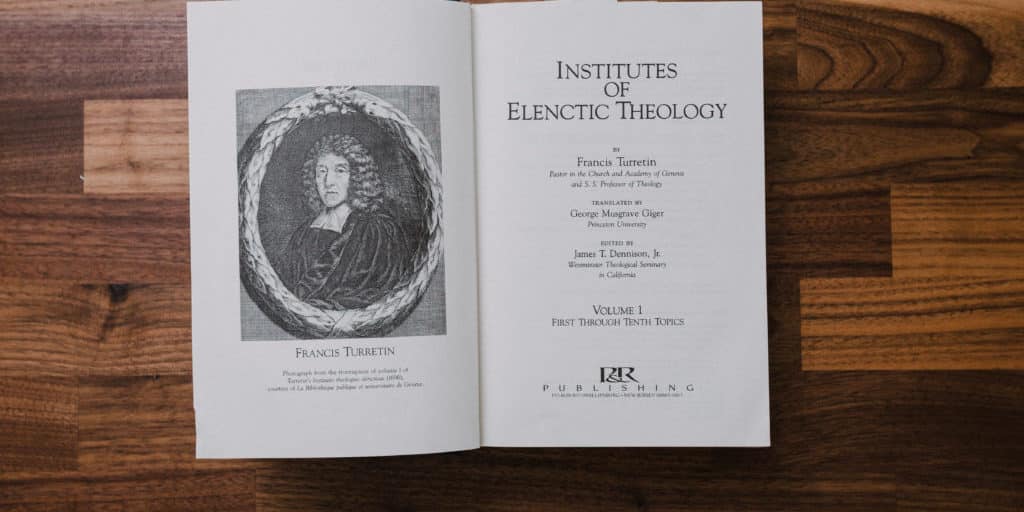第一要点:神学
第五问:神与神圣之事是否为神学的对象?我们对此予以肯定。
神学的对象
一、任何科学的对象,都是指该学科专门探讨的内容,以及与其结论相关的一切内容;但此对象可从两方面考察:质料层面(materialiter),即所论之事物本身(rem consideratam);与形式层面(formaliter),即考察的方式(modum considerandi)。
二、尽管神学家对神学对象的界定存在分歧,但更普遍且正确的观点认为:神学的对象是神与神圣之事(Deum & Res Divinas);神为首要对象,神圣之事为次要对象,要么是神所行之事,或者是人当信或当行之事。换言之,神学直接讨论神本身,间接讨论与神相关之事(quae Dei sunt),如祂的作为、隶属于神的,如受造物、以及趋向神的,如人的责任(hominis officia)。因此,神学所论之事,要么是其关乎神自身,要么是它们与神这位第一因与终极因存在关联。
三、神作为神学的对象,这一点可从以下方面得到明证:首先,从名称本身可知——”神学”(θεολογίας)与”敬畏”(θεοσεβείας)二词已显明其本质;其次,从圣经,圣经明确认定除神以外别无其他首要对象;此外,从研究对象的条件,即神完全符合作为神学研究的对象所应具备的条件:(1)祂是单纯非复合的实体(aliquid incomplexum);(2)可用语言赋予属性称谓,如情感与特性;(3)在学科体系内的一切皆与之关联——因神乃是非复合的、最纯一的存有(Ens incomplexum & maximè simplex)1,其属性皆可被述说(如祂的诸般完美特性),万有都因起源、维系与依存关系而归于祂。
作为启示与立约的神
四、当我们将神确立为神学对象时,不可仅将其单纯的视为“神在其自身所是”(Deus in se),因为神在其自身对我们而言是不可透知的(ακατάληπτος),而应当视为照着神的启示程度而认识的神(quatenus revelatus),即那位按自己美意在圣道中向我们显现的样式。因此,神圣的启示构成了我们获取这一对象的形式性原理(ratio formalis)。我们也不应像托马斯·阿奎那及其后的许多经院学者那样,仅仅从神性角度来认识神(ratione Deitatis),因为这种认知对罪人而言非但不具救赎性,反致灭亡,而应当认识那位”我们的神”(Deus noster)——即在基督里与我们立约的神(foederatus),祂在圣言中向我们启示自己,不仅是认知的对象(ut cognoscendum),更是敬拜的对象(ut colendum)。神学所教导的真宗教敬虔(Religio)是由这两个方面构成的。
解答的根据 (fontes solutionum)
五、一门科学的统一性及其与其他科学的区别,并非总是取决于其质料对象(Objecti materialis)或者说所考察的事物本身的统一性,而是取决于其形式目的(Objecti formalis)或者说考察方式(modo considerandi)的统一性。虽然物理学、伦理学和医学都研究同一个主体,但它们仍然是不同的科学,因为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人的:物理学将人视为一种自然物体;伦理学将人视为能够获得美德与幸福的主体;医学则将人视为能够治愈疾病、恢复健康的对象。同样,虽然神学与形而上学、自然科学和伦理学讨论相同的事物,但其考察方式却大不相同。神学讨论上帝时,不像形而上学那样将其视为”存有本身”(Ens)或可以通过自然理性认识的对象,而是将其视为通过启示所显明的创造者和救赎主。神学讨论受造物时,不是将其视为”自然事物”(res naturae),而是视为”属于上帝之物”(res Dei):即与上帝——它们的创造者、维系者和救赎者——具有特定关系和秩序的存在,并且这种讨论完全是基于上帝所启示的真理。这种考察方式是其他科学既不了解也不采用的。神学讨论上帝时,不像形而上学那样将其视为”存在本身”或可以通过自然理性认识的对象,而是将其视为通过启示所显明的创造者和救赎主。神学讨论受造物时,不是将其视为自然存在,而是视为”属于上帝之物”(即与上帝——它们的创造者、维系者和救赎者——具有特定关系和秩序的存在),并且这种讨论完全是基于上帝所启示的真理。这种考察方式是其他科学既不了解也不采用的。
六、神学论证上帝存在并非出于首要或本然意图,而是出于某种偶然的必要性,即为了驳斥那些没有羞耻、良心被烙一般的亵渎者与无神论者。(2) 所谓”科学不证明其研究对象,而是预设其存在”这一公理,仅适用于人类与低等科学,却不适用于神学。神学属于更高层的科学,因它能凭借自身特有的方式(即神圣启示)论证一切可证之事。这种论证并非工具性的(instrumentaliter),而是具有建构性的权威(architectonicè)。
七、一门科学体系不必完全把握其研究对象的所有方面,只要能够认识其中的诸多内容,并能从其原则进行推导便已足够。因此,科学与其对象之间无需达成精确的、算术般的完全对等(secundùm exactam & arithmeticam aequalitatem),只需保持某种相称的对等关系即可(secundùm aliquam aequalitatis proportionem)。这种对等关系在神学中确实存在:神学虽然探讨上帝及其无限完美,但并非以无限的方式认识,而是以有限的方式;不是绝对地认识其全部可知性,而是按照上帝所启示的程度。因此,神学可被视为与其对象形成形式上的对等(secundùm formalem rationem revelationis)——这种对等不是与上帝本身的对等,而仅是与上帝所赐启示的对等。
八、通常认为科学只研究共相(universalium,或译作事物的普遍性)而非殊相(singularium,或译作事物的特殊性),这一说法不应全盘接受。因为形而上学、物理学等学科虽为科学,却同样探讨个别事物——如上帝与世界。这条公理应理解为仅适用于由质料构成的、处于最低物种中的个别事物。至于神学中涉及的个别对象(如亚当、挪亚等),其研究并非主要目的,而是为了追溯事物起源、作为生命典范、见证神圣护理,或是基于普遍原因。然而,若涉及非物质性以及纯粹现实性的个体(in actu puro)2,即如上帝,则毫无疑问可成为科学对象,因为理智的对象是”存有”(Ens);存有愈完美,就愈能被认知;而愈接近纯粹现实性(actu)、远离潜在性(potentia)的存在就愈完美。(2)上帝理应归入普遍者之列:在因果层面,祂是万物的普遍原因;在谓述层面,虽非直接谓述(因万物不等同于上帝),但万物皆属上帝、源自上帝、归向上帝。因此,神学对象在这方面同样具有普遍性的全部理据。
九、在较低级的科学中,科学的原理(principia scientiae)必然不同于其研究对象——这些原理需通过自身特性来证明研究对象的属性与特征。因为任何人类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有限本质与能力的实体,必须依赖某些原理作为其来源或构成基础。但属于更高层级的神学则拥有全然神圣的研究对象,其本质与能力皆为无限,是绝对先在者,故不可能具有任何被原理化的性质。正因这种无限性,神学的研究对象同时包含双重属性:它既是神学探讨的主题(subjectum),又是神学自身的原理(principium)。
十、神学论及罪(peccato),并非着眼于神本身(prout Dei),而是着眼于罪与神的特定关系(prout quandam σχέσιν ad Deum habet):或作为与神对立且相悖的存在,或作为受制于神圣护理与公义审判的对象。正如医学虽以治愈健康之人为首要目标,却仍需研究疾病与毒物一般。
- 在1688年第二版的Institutio中,出版商把incomplexum 错拼成incompletum。 ↩︎
- 译注:图伦庭在这里使用了经院主义神学中的区分,即存有的现实性和潜在性的区分(actu/potentia,英文作act/potency)。上帝与受造物不同,上帝不存在潜在性(potency),因此是上帝是纯粹的现实性(pure act,或作pure actuality)。 ↩︎
作者:图伦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