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人认为,以色列的民族地位及其在应许之地上的产业取决于他们的顺服或悖逆。然而,这种观点近年来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能详细阐述一下这句话吗?
在改革宗神学的历史中,对于摩西之约有多种不同的表述方式。改革宗普遍认同摩西之约是恩典之约的一种施行方式。争议在于如何描述摩西之约与行为之约之间的关系。
在16、17世纪,改革宗作家普遍将摩西之约(或称旧约)称为“律法之约”,并将其与亚当的行为之约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摩西之约具有显著的律法性,以至于他们引以为据来证明堕落前必然已与亚当立有行为之约。由于与宗教改革时代相距不远,他们对“律法之约”较为敏感,毕竟他们刚刚脱离一个长达近千年的体系,该体系声称人被上帝接纳的条件是上帝的恩典以及人的合作(即行为)。尽管中世纪强调恩典,但其教义究其根本仍是凭律法之约而蒙上帝接纳,因为该约的本质在于人的配合与行为。直到现在新教对罗马天主教的批评仍针对于此。
改革宗肯定律法的正常功用,但他们一眼就能认出律法性的约定,而在摩西之约中他们看到了大量律法性的、条件性的语言: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就是律法,也是律法性条件(申27:26;加3:10)。
因此,他们普遍认为摩西之约具有某种律法性特征,但他们不会说摩西之下的人是靠律法而被上帝接纳(即称义)。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摩西之约中的律法性(例如那613条律法)的目的,是为了将摩西、大卫及先知时期(约1500年)的罪人引向基督。我们称此为律法的第一功用。他们认为民事律是为了规范以色列的社会生活。这是律法的第二功用。他们认为道德律(包括所有律法中的道德层面)是为了规范信徒的生活。他们一致认为,在基督里,民事律与礼仪律已经被废除和成全,十诫中的礼仪和民事层面也都被废除和成全,但概括于十诫中的道德律仍然有效,因它根植于创造。
从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等人多年来在海德堡博客上的引文可以看出,一些作者不仅将摩西之约视为行为之约的再版,还认为以色列的民族地位及其在应许之地的居留权,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他们对律法的顺服为条件的。不过并非所有16、17世纪作家都同意这一观点。
然而,到了19世纪,时代论者开始以一种相当激进的方式将圣经划分为七个不同的时代。时代论成形于1830年代,改革宗作家在此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谈论过恩典之约的不同“时代”或曰施行阶段(如: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但时代论者的“时代”并非指恩典之约的不同施行方式,而是指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上帝在每个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人类,其中的救恩方式也各不相同。
改革宗作家强烈反对这种撕裂救赎历史整体统一性的做法。时代论自形成至今已经历至少两次重大修正:即“修正时代论”(如查尔斯·雷里Charles Ryrie)和“渐进式时代论”。这两个后来的版本与原版时代论都一致认为上帝有两个并行的子民:以色列与教会。
为了回应这一极为流行的解经进路,许多20与21世纪的改革宗作家开始淡化摩西之约与新约之间的区别。与此同时,改革宗信徒也逐渐遗忘更古老的圣约神学(救赎之约、行为之约、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几乎已吞并另外两约。到20世纪,改革宗作家中已很少有人阐述行为之约或救赎之约。到1970和1980年代,某些圈子甚至以否认行为之约为“正统”。因此,将摩西之约视为行为之约的“再版”在当时就显得非常荒谬,对有些人来说简直是离经叛道。
有人认为,如何看待再版取决于如何看待行为之约。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坚定持守行为之约教义的人,也会支持再版论;而不赞成行为之约的,自然也会质疑一切再版教义。我不确定这一分析是否完全成立,但在某些情况下似乎确实如此。
还有一些人反对所谓的“试验性模式”(probationary model)是因为担心这种模式会将他们从19世纪批判至今的时代论引入改革宗神学。然而,这一反对忽略了一个区分,即试验性模式(土地产业/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对律法的顺服)的支持者清楚区分了唯独恩典、唯独信心的称义和以色列的土地产业/地位。
对此概念(即以色列之土地产业及民族地位端赖顺服)的另一批评是:这是一种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即认为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讨神喜悦。这些批评者认为,若说以色列的土地产业/地位端赖顺服,就等于把“人的功德“的观念重新引入新教神学,
而关于任何人之功德的任何谈论,都是对改革宗神学的腐蚀。有些人还声称,基督的功德是基于他的神性而非祂的顺服。然而,这种观点在改革宗信条中未见清晰表述,古典时期的改革宗正统神学也未广泛教导(若曾有过)。改革宗正统如何讲述基督功德可从《韦修斯论功绩》一文略见一斑。
我认为,双方大都承认,试验性的土地产业不可能完全是律法性的。有些试验性模式的支持者可能过于强调土地产业的律法层面,以至于忽视了恩典在其中的作用。
以色列犯罪如此之多,而主对他们如此恩慈与忍耐,所以我们无法将土地产业视为有严格的律法性。如果真有严格的律法性,以色列根本就无法进入那地,也不可能久居其上。这产业肯定不是全靠功德,不过摩西五经中确实有严格的律法性语言,指明以色列若想继续居留那地当如何行,以及若不遵行将会有何后果。这些语言显然具有“试验性”特征。
一些试验性模式的批评者认为,上帝与罪人之间惟靠恩典才能建立关系,无论是关乎称义,还是关乎以色列的土地产业或民族地位。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只要宣称以色列的土地产业或民族地位取决于顺服,就必定是在否认恩典。
故此,一些问题在17、18或19世纪并无争议,但在20世纪却被遗忘,如今便因着种种原因再度引发争议。
译者:Lois
英文原文:https://heidelblog.net/2013/08/more-questions-from-ginger-why-is-republication-so-controversial/
作者:司考特·克拉克

司考特·克拉克博士(Dr. R. Scott Clark),加州西敏神学院(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教会历史与历史神学教授;曾任教于惠顿学院、改革宗神学院杰克逊校区、协和大学等多所院校;著有《恢复改革宗信条》,《卡斯帕·奥勒维与圣约的实质》等书;其个人博客为Heidelblo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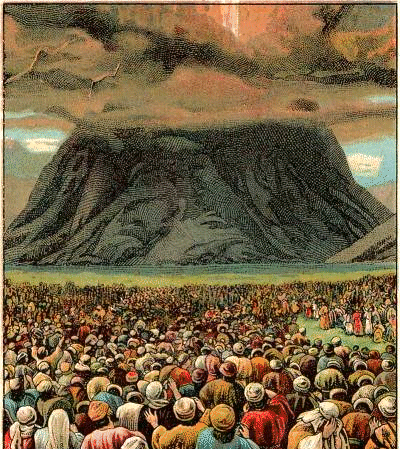
b3qpoe
twyai6
y1ifwk